永远的现代 高耸的北山——施蛰存先生铜像前的感怀 文/胡绳樑
牛年二月,寒意渐衰。施蛰存先生如在世已百又五年。连日疾雨劲风,这天却雨歇风轻。与一干作家朋友去上海福寿园谒这一现代文坛的“大学家”长眠之地,老天也开眼,阳光恰在这一刻拨开阴云。
施蛰存先生的铜像端坐在知博苑那片四季常青的大草坪上。一把藤椅,一支雪茄,九十九岁的世纪老人仙逝后就这样在这里久久地“坐”看千古风云。那神态、那模样一如其生前。铜像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手笔”,摹形亦传神。突然,想比附施老“新感觉派”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潜意识、意识流:他没有“走”,不过是把北山楼寓所书桌前的那个藤椅挪到了这里而已。

施蛰存先生的铜像·知博苑
那种从容淡定,那种睿智优雅,不由让我想起在1997年6月27日 登“北山楼”拜访施老的情景。
愚园路临街的那幢英国式小洋楼因住了施蛰存而吸引了海内外的不少访者。为请施老给自己责编的报纸副刊“文华”赐稿,提前几天去电施老家预约,因施老耳背而与他家里人敲定了上门拜访的时间。
那天下午先是找到了施家楼下的邮局,拐个弯从后门入。沿窄窄暗暗的木梯上去,像是穿越历史隧道似的,豁然洞见施老号为“北山楼”的那间约二十平方米兼书房兼饭厅兼卧室的会客室,陈旧简陋的书柜紧挨在典雅的西式壁炉旁,与书桌的距离也仅在一椅之间。惊讶于一代文学大师竟蜗居于这么逼仄的空间。
人生的空间有限,人类的精神无限。学问与生存条件并非正比的关系。
施老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以微笑相迎,我趋前大声说明来意,施老客客气气地让我坐在旁边。我将带来的一些“文华”副刊样报递给施老,施老兴味盎然地浏览了一番,并重点看了几篇,放下报纸便连声称赞道;“我平时看不到劳动报,现在看看你们的副刊办得蛮不错,名家、新人都有,内容蛮丰富的么!”于是他十分爽快地说:“有空一定给你们投稿!”接着我用笔写,施老大着嗓门答,基本都是鼓励我们的意思。聊了几句,施老便从背后的书架上取了一册他选定的《花间新集》,很认真地写下了“绳梁同志正之”并签了大名赠我。不久我收到并编发了施老那篇《大起大落说收藏》的大作,后来我作为《点燃欢乐——〈劳动报〉五十年文粹》的主要编选者又将其收入了纪念文集。
与施老见面时间不长,但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慈眉善目,温文尔雅。那种“雅逸”是经年累月修养涵养的积淀。从“飘飘荡荡的大少爷”到“学富五车的大学家”,那种大智那种大雅早已成为他骨子里的精髓了。
他在1996年曾经对一位美国的华人学者孙康宜谈起他的人生态度:“我从不与人争吵,也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当作一回事。在‘文革’期间,我白天被斗,晚上看书,久而久之我就把这种例行公事看成一种惯常的上班与下班的程序……总之,无论遇到什么运动,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就可以回家去读自己的书了。”
他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对政治运动“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这是经历了大苦大难后的大彻大悟?总觉得他的隐士思想与当年那种“第三种人”的理念有着某些若隐若现的关联。
他早已不与世争,只与学术争。 心定天地宽,他的文化成就如此之“庞杂”,或许和他晚年与繁杂的世事无涉不无关系。心静万事和,他的长寿,当然也与其平静淡定的心境有关。
施老曾以诗句作陋室铭:小楼一角成高隐,回首前尘百事非(施蛰存诗:“浮山杂论”四十五)。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异曲同工?
“为了忘却的记念”?不是所有的记念都会被忘却的,许多事经历过一次却会影响一生。
面对中国新感觉派心理小说的鼻祖,心里似乎又有了一种“新感觉”:鲁迅的铜像也有坐在藤椅上的,不同的是鲁迅的神态更理性些,施蛰存的表情更知性些。鲁迅习惯抽香烟,施蛰存偏爱抽雪茄。同样在老上海的土地上,一个用贴近政治的笔锋以革命的思想抨击现代;一个用贴近艺术的笔调以传统的思想诠释现代。别人都以为这两位大师因为《庄子》与《文选》的争论而水火不相容,其实未必。施蛰存的儿子施达先生前些天在他建国西路家中的三楼居室里亲口告诉我:两人“吵”了后,他父亲还请鲁迅吃饭呢!没像别人所误解的到了完全势不两立的地步。据施达说:在争论处在很激烈的时候,当他父亲真正得知批评者是鲁迅时(尽管他从文风中已揣测到批评者可能是鲁迅,但他“少年意气”,也回击过不少“过头话”),就马上搁笔,并向鲁迅赔礼道歉,这样争论也就很快停歇了。
施蛰存曾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不敢发的鲁迅那篇战斗檄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胡乔木在1989年深秋到北山楼访晤施蛰存时,赞誉其“立了一功”。或许后来的那场争论真的是一场误会,而且现在回头看去其激烈到如此程度也无甚多大意义。但这场争论确确实实影响了施蛰存的人生道路,亦是造成不少坎坷或明或暗的原由。不管后人对此有多少种揣测、分析或者批评,我还是相信施老对鲁迅心怀崇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施老在虹口公园瞻仰鲁迅铜像后曾作《吊鲁迅先生诗》及序,表达了各自宏文、宏道的志趋:“殊途者同归,百虑者一致”。施老曾经对他的一位学生说:“我从来尊重鲁迅,连‘腹诽’都没有过……”
原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徐中玉教授的评判很有道理:“鲁迅唯恐青年陷入古书堆中出不来,蛰存觉得青年写作词汇贫乏,可以从古书中吸取语言材料。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其善意在……”
施老曾说过很有点沉痛的话:鲁迅是从抄古碑的生活中走向革命,而他自己则从革命走向了抄古碑。联想施老曲曲折折的人生,这话让人回味的余地很多……
“我欲呵天问,滔滔逝水流”(北山楼诗句)。施老铜像前面不远处横陈着一条河,清清浅浅却蜿蜒曲折得很,多少名人沿着岸线在这同一片大地中安息。静静的,历史就在他的脚下如水一样地流淌。多少往事随着他手指间的雪茄,轻烟似地随风而去。
历史已经不再沉重。
沉重的是那些写历史的人。
鲁迅是座山,如果不以“革命”论英雄,在文化成就上施蛰存难道不是一座峰?!
虽然人生不能简单的类比;虽然施蛰存的人生曾经被无情地扭曲,但岁月的春风终究会涤去尘埃。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艺思潮史上,施蛰存几乎是招致最多左翼批判而自己始终形单影只的作家。特立独行,或许就是施蛰存人生历程中的标签。
历史曾经无言,但史家自有公论。
施蛰存曾在《说说我自己》一文中为自己拟了墓志铭:“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降二级录用——施蛰存之墓。”
这种幽默谁都能体悟其中苦涩。
1957年始,戴帽“右派”,屡屡挨批;1966年,又被批又被斗。漫漫二十余年,不能出书,不能发表文章,只能接受劳动改造。他的不堪遭遇与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相差无几,但由于曾与鲁迅的一争而不幸更甚。
有人说,这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就是一个“默存”,一个“蛰存”。语虽近谑,含义沉痛。施先生名“蛰存”,此“蛰”似有点“冬眠”的意思,“蛰”是为“存”,也能积蓄能量,这也是劫后余生的不少知识分子后来大“施”身手做出巨大贡献的前因一种。
好在历史的遭遇不等于结论。
盖棺论定,这论是历史立的,是人民定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海派文化标志性人物”,1993年,施蛰存先生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这是颇有官方色彩的褒奖。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是有国际影响的奖项。其实他的赞誉更多地来自方方面面:“百科全书式的专家”、首位 “资深翻译家”、“中国新文学大师”,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派鼻祖”、“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新感觉派大师”。
真正的大师不是捧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施先生的等身著作与开创性的学术成就是奠定他作为“文坛巨星、学界泰斗”地位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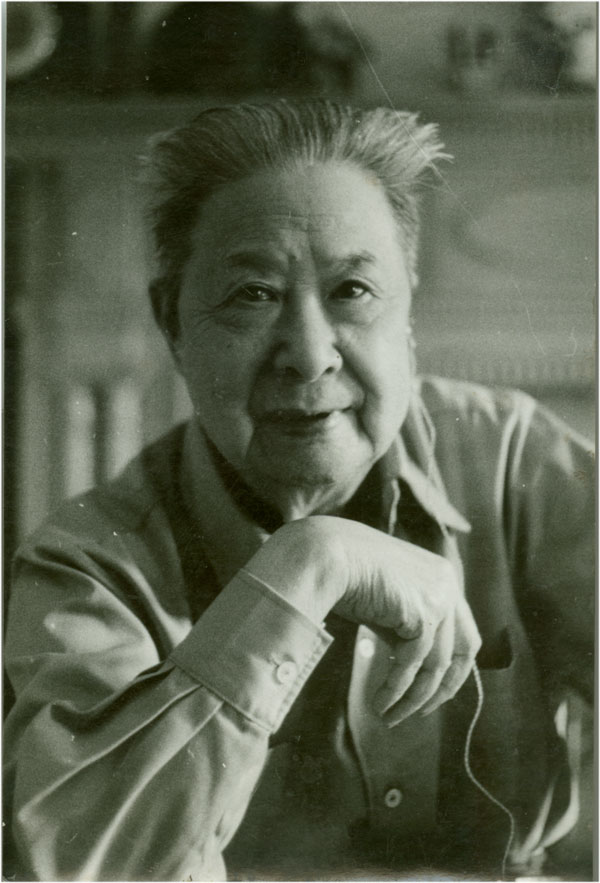
施蛰存(1905.12.3——2003.11.19)
17岁投身文学与教育园地,笔耕生涯80年,学融中西,道贯古今。小说、旧体诗、现代派诗、译著、古籍整理、金石碑版考察、文学理论研究等等,其涉及领域之广之杂在当代中国似乎无人出其右。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印行过9个单行本。翻译的长短篇小说也有20余种,他在唐诗、宋词、金石碑版方面已出版的专著亦达10多种,他发表的散文随笔更是难计其数。《唐诗百话》在美国被耶鲁大学选为教材;《唐碑百选》、《金石百咏》、《文艺百话》、《浮生百咏》等构筑了其“百字辈”的系列作品。
脚踏中西两头船,文开北山四扇窗。
施老曾将自己的文字生涯喻为一生开了四扇窗,这一生动扼要的总结也得到了施学研究者的一致认可。“北山四窗”可以大致概括施蛰存的重大文化成果。“北山”是施蛰存的“号”,也是其“蛰”居做学问的小楼斋名。“四窗”,即以中国文学为主的东方文学研究为“东窗”;以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为“西窗”;以灿烂的文学创作为“南窗”(或许是因为其小说创作辉煌,如家居从南面投进的阳光格外灿烂);以金石碑版考察为“北窗”(此是冷门学科,或许寓意风从冷僻之地来)。
其常被人赋予的冠冕亦有四:文学家、编辑家、教育家、翻译家。名至实归,名副其实。
一生四窗,百年千古。华东师大中文系早在1997年就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可施老生前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他的名片上只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这一个职衔。
施老在2002年李欧梵先生从美国过来拜访他时说:“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施蛰存的谦逊历来为人称道,但他的自谦背后却是骄人的底气。他的成就是跨世纪的,沉寂过后老来更“红”。
1993年,施蛰存先生在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颁奖会上发言说:“应该多奖励青年人,对我这样的老人就不需要什么奖励了。”再显施老处世淡然的本色。
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是不会过时的。施蛰存先生的文化建树已被视为现代文化的历史碑刻。人们对他的追忆多多,就源于其丰富多彩的杰出贡献。200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其中那些回忆施老的文章,感人肺腑。
对施老最好的奖励莫过于对他文化遗存的发扬。据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筹备出版《施蛰存全集》。湖北与上海的学者几乎是同步在撰写《施蛰存传》。海内外有几多莘莘学子以施蛰存作为研究的课题。
人生成就如斯,能不令人仰视?!
陈子善认为:施蛰存研究还起步不久,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开拓,施蛰存其实也是说不完的。
施老驾鹤西去后,有一本记忆施蛰存的文集名曰《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其实施蛰存何尝不是现代文坛永远的一朵玫瑰啊。
施老的铜像与石碑立在福寿园,也在敬重他的人心里。
心中的铜像才是真正不朽的。
本文作者:胡绳樑,上海作家,《劳动报》副刊部主任。





